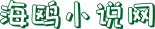“恩?颜宫?”星旧倒了一杯茶放到聂磐面前,“为何?”“说来惭愧...”聂磐摸到茶杯,抿了一口,“至今瞎子都未曾告诉族长自己的身份,其实...我便是...”说到此处,聂磐手指沾着茶水在桌面上画了两个字——红眸。
“聂磐,所谓天机不可泄露,外人之事可是要牺牲自己的元寿才可窥其一二。”星旧抿了口茶,看着桌面上的字,不着痕迹地擦去,淡淡地回答。“不必详细,只须知道可会安全,还望族长成全聂磐。”聂磐听得出星旧语气中的顾虑。“伸手。”星旧微微叹了口气,“不须你说,其实我早已测过。”
“还请族长详说!”听了星旧的话,聂磐心中一喜,连忙伸出右手。随着星旧在他的手心慢慢画字,聂磐脸色变得有些凝重。险象生还。这是星旧在聂磐手心画出的字。“果真是如此......”聂磐喃喃自语,又自嘲地笑笑,“若不是我现身,怎会有诸多事端?”语罢,一股阴冷的气息慢慢开始在聂磐的周身环绕,一团黑气爬上眉心。“聂磐,可否听我一句话?”星旧看着喃喃自语的聂磐。“族长请讲。”聂磐回过神,作出请的手势。“命里有时终须有,命里无时莫强求。莫要徒增悲伤。”星旧说这句话时,声音苍老的仿佛油尽灯枯。但这苍老的声音却在聂磐的脑中回荡炸响,如同洪钟鸣响。
“族长教诲的是。”聂磐惊得一身冷汗,稍稍运气,收回外溢的煞气,“多谢族长。”“说笑了,此行我还得依仗你。”星旧眯起眼睛抿口茶,笑了笑,“算是互帮互助。”“哈哈哈”聂磐也是不拘小节的人,边笑着边起身,“好一个互帮互助,事不宜迟,我去准备些路上要用的东西,族长你收拾一下行礼,我们择日出发。”“有劳,不送。”星旧拱了拱手,目送聂磐离开。
就在聂磐离去后不久,隼人长老从房子的死角处走出来,脸上带着阴冷的笑容,寻了一个无人的角落,偷偷地放出一只信鸽。殊不知,就在他看着信鸽飞远的时候,一道无形的煞气,已经藏入了自己心脉中。
星旧在房中喝了一口茶,微微一笑:“这一手...聂磐,我还是小看你了。”语罢,又自嘲地笑了笑。此时,聂磐站在窗前,脸上露出一丝杀机:“啧...颜肆厥啊,赌命,我看你敢不敢和我赌。”
皇城,御书房
颜肆厥坐在椅子上,看着面前的沙盘,眉头紧锁。“倾门,沙海...可真是名副其实啊...”良久,颜肆厥倒吸了一口凉气。“若想掌控天下,必要有所舍得。”颜倾门看着沙海的地形,也是一脑门的冷汗,“此行埋伏,还望陛下要慎重选人。”“孤明白,樊夜手中还有多少人马?虽说孤想夺得国运大鼎,可这边疆周遭的豺狼虎豹却也一刻不得放松啊。”颜肆厥揉了揉太阳穴。“还有一万人马。另外,陛下,可否动用十八血骑?”颜倾门看着手中的书册,试探性地问。“先让樊夜率兵前去,十八血骑...还需等得清弦归来。”颜肆厥摇了摇头,“十八血骑,见主而动,清弦未归,孤也请不动他们。”“如此......倾门还得多叮嘱樊将军多做些准备。”颜倾门躬身出了御书房,“倾门先行告退。”
颜肆厥孤身坐在沙盘前,阳光透过窗户慢慢打进房内,一道修长的身影投影在书房的侧墙上,隐约像一只吞噬灵魂的巨兽正缓缓张开嘴......